重症急性胰腺炎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
DOI: 10.12449/JCH240608
Guidelines for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
摘要: 重症急性胰腺炎起病急、进展快,临床病理变化复杂,病死率高达20%~30%。长期的临床实践与基础研究发现,单纯依赖西医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并不尽如人意,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够展现出更为确切的疗效,具有显著的优势。本指南以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结合国内外指南及临床实践,广泛征求专家建议与意见,最终凝练了28个临床问题。具体阐释了重症急性胰腺炎的病因病机与诊断标准,以及中西医结合分型、病程分期、治疗与治疗的关键点,以期对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中西医结合诊断标准和治疗原则进行规范。该指南经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标准编号:T/CACM 1518—2023。Abstract: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is characterized by rapid onset and progression, complex clinico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a mortality rate of as high as 20% — 30%. Long-term clinical practice and basic research have shown that relying solely on Western medic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SAP may not achieve satisfactory outcomes, and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has a marked clinical effect and significant advantages. Based on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nd with reference to related guidelines and clinical practice in China and globally, these guidelines summarize 28 clinical questions after widely soliciting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rom experts. This document specifically elaborates on the etiology, pathogenesis,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SAP, as well as the key points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yping, disease staging, treatment methods, and therapies, so as to standardize the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treatment principles of SAP.
-
表 1 AP分类诊断系统
Table 1. Diagnostic system for classification of acute pancreatitis
分级系统 轻症 中度重症 重症 危重症 RAC分级1) 无器官功能障碍和局部并发症 出现一过性(≤48 h)器官功能障碍和/或局部并发症 出现持续性(>48 h)器官功能障碍 无 DBC分级2) 无器官功能障碍和胰腺(胰周)坏死 出现一过性(≤48 h)器官功能障碍和/或无菌性坏死 出现持续性(>48 h)器官功能障碍或感染性坏死 出现持续性(>48 h)器官功能障碍和感染性坏死 注:1)RAC分级,即修订版Atlanta分级,依据改良Marshall评分进行器官功能障碍诊断;2)DBC分级,即决定因素的分级,依据序贯器官衰竭评分系统进行器官功能障碍诊断。
表 2 改良CT严重指数评分1)标准
Table 2. Scoring criteria for the modified CT severity index
特征 评分(分) 胰腺炎性反应 正常胰腺 0 胰腺和/或胰周炎性改变 2 单发或多个积液区或胰周脂肪坏死 4 胰腺坏死 无胰腺坏死 0 坏死范围≤30% 2 坏死范围>30% 4 胰外并发症2) 2 注:1)改良CT严重指数评分为炎性反应、坏死与胰外并发症评分之和;2)胰外并发症包括胸腔积液、腹腔积液、血管或胃肠道受累等。
表 3 BISAP评分
Table 3. BISAP scores
符合以下每项标准评1分 评分(分) 血尿素氨>8.9 mmol/L 1 精神异常 1 存在SIRS 1 年龄>60岁 1 影像检查提示胸腔积液 1 表 4 SAP中医辨证分期的论治
Table 4. Treatment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with Chinese medicine identification and staging
病程分期 病理改变 临床表现 中医辨证 治则 代表方剂 第一期 无菌性胰腺胰周坏死、无菌性炎性阶段 急性坏死物积聚、ACS、SIRS、MODS、急性胃肠功能损伤 正盛邪实、少阳阳明合证、阳明腑实证、结胸里实证 通里攻下、活血化瘀 大承气汤、清胰陷胸汤 第二期 感染性胰腺胰周坏死、感染性炎症阶段 脓毒症、代偿性抗炎反应综合征、重症监护后综合征、MODS、包裹性坏死、感染性胰腺坏死 热结腑实、毒热炽盛 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通里攻下 清胰汤、清胰承气汤 第三期 残余感染性胰腺胰周坏死、局部并发症、内分泌功能损伤、外分泌功能损伤 营养不良、局部并发症 正虚邪去、正虚邪恋、正虚邪陷 补气养血、健脾和胃 辨证方剂 -
[1] CUI NQ, QI QH, KONG D, et al. Treatment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with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 report of 145 cases[J]. Chin J Surg Integr Tradit West Med, 1999, 5( 3): 129- 132.崔乃强, 齐清会, 孔棣, 等. 重型急性胰腺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附145例报告[J].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1999, 5( 3): 129- 132. [2] XIA Q, HUANG ZW, JIANG JM, et al.“Yi-Huo-Qing-Xia” method as the main therapy in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o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A report of 1 161 cases[J]. Chin J Integr Tradit West Med Intensive Crit Care, 2006, 13( 3): 131- 134. DOI: 10.3321/j.issn: 1008-9691.2006.03.001.夏庆, 黄宗文, 蒋俊明, 等. 以“益活清下”为主的中西医结合综合疗法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1 161例疗效报告[J].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06, 13( 3): 131- 134. DOI: 10.3321/j.issn: 1008-9691.2006.03.001. [3] HU Y, JIANG X, LI CY, et al. Outcomes from different minimally invasive approaches for infected necrotizing pancreatitis[J]. Medicine, 2019, 98( 24): e16111. DOI: 10.1097/MD.0000000000016111. [4] LIU XY, CUI YF. Individualized surgical intervention i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J]. J Hepatobiliary Surg, 2019, 27( 6): 474- 478. DOI: 10.3969/j.issn.1006-4761.2019.06.022.刘翔宇, 崔云峰. 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个体化外科干预[J]. 肝胆外科杂志, 2019, 27( 6): 474- 478. DOI: 10.3969/j.issn.1006-4761.2019.06.022. [5] CUI YF, QU ZL, QI QH, et al. Guidelines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with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Tianjin, 2014)[J]. Chin J Surg Integr Tradit West Med, 2014, 20( 4): 460- 464. DOI: 10.3969/j.issn.1007-6948.2014.04.049.崔云峰, 屈振亮, 齐清会, 等. 重症急性胰腺炎中西医结合诊治指南(2014年, 天津)[J].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2014, 20( 4): 460- 464. DOI: 10.3969/j.issn.1007-6948.2014.04.049. [6] BANKS PA, BOLLEN TL, DERVENIS C, et al. Classification of acute pancreatitis: 2012: Revision of the Atlanta classification and definitions by international consensus[J]. Gut, 2013, 62( 1): 102- 111. DOI: 10.1136/gutjnl-2012-302779. [7] ZHANG SS, LI HZ. Consensus opinion of TC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xperts on acute pancreatitis(2017)[J]. China J Tradit Chin Med Pharm, 2017, 32( 9): 4085- 4088.张声生, 李慧臻. 急性胰腺炎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2017)[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7, 32( 9): 4085- 4088. [8] Digestive System Disease Committee of Chinese Association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Consensus 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cute pancreatitis with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2017)[J]. Chin J Integr Tradit West Med Dig, 2017, 25( 12): 901- 909. DOI: 10.3969/j.issn.1671-038X.2017.12.03.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 急性胰腺炎中西医结合诊疗共识意见(2017年)[J].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2017, 25( 12): 901- 909. DOI: 10.3969/j.issn.1671-038X.2017.12.03. [9] BOXHOORN L, VOERMANS RP, BOUWENSE SA, et al. Acute pancreatitis[J]. Lancet, 2020, 396( 10252): 726- 734. DOI: 10.1016/s0140-6736(20)31310-6. [10] DELLINGER EP, FORSMARK CE, LAYER P, et al. Determinant-based classification of acute pancreatitis severity: An inter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consultation[J]. Ann Surg, 2012, 256( 6): 875- 880. DOI: 10.1097/SLA.0b013e318256f778. [11] van DIJK SM, HALLENSLEBEN NDL, van SANTVOORT HC, et al. Acute pancreatitis: Recent advances through randomised trials[J]. Gut, 2017, 66( 11): 2024- 2032. DOI: 10.1136/gutjnl-2016-313595. [12] YOKOE M, TAKADA T, MAYUMI T, et al. Japanese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pancreatitis: Japanese Guidelines 2015[J]. J Hepatobiliary Pancreat Sci, 2015, 22( 6): 405- 432. DOI: 10.1002/jhbp.259. [13] STAUBLI SM, OERTLI D, NEBIKER CA. Laboratory markers predicting severity of acute pancreatitis[J]. Crit Rev Clin Lab Sci, 2015, 52( 6): 273- 283. DOI: 10.3109/10408363.2015.1051659. [14] CHO JH, KIM TN, CHUNG HH, et al. Comparison of scoring systems in predicting the severity of acute pancreatitis[J].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5, 21( 8): 2387- 2394. DOI: 10.3748/wjg.v21.i8.2387. [15] HINES OJ, PANDOL SJ. Management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J]. BMJ, 2019, 367: l6227. DOI: 10.1136/bmj.l6227. [16] WU XZ, WANG PZ. Practice of abdominal surgery[M].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7.吴咸中, 王鹏志. 腹部外科实践[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17] LEPPÄNIEMI A, TOLONEN M, TARASCONI A, et al. 2019 WSES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J]. World J Emerg Surg, 2019, 14: 27. DOI: 10.1186/s13017-019-0247-0. [18] TENNER S, BAILLIE J, DEWITT J, et al. American College of Gastroenterology guideline: Management of acute pancreatitis[J]. Am J Gastroenterol, 2013, 108( 9): 1400- 1415, 1416. DOI: 10.1038/ajg.2013.218. [19] HOWARD TJ, PATEL JB, ZYROMSKI N, et al. Declin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rates in the surgical management of pancreatic necrosis[J]. J Gastrointest Surg, 2007, 11( 1): 43- 49. DOI: 10.1007/s11605-007-0112-4. [20] YANG AL, MCNABB-BALTAR J. Hypertriglyceridemia and acute pancreatitis[J]. Pancreatology, 2020, 20( 5): 795- 800. DOI: 10.1016/j.pan.2020.06.005. [21] DUBINA ED, DE VIRGILIO C, SIMMS ER, et al. Association of early vs delayed cholecystectomy for mild gallstone pancreatitis with perioperative outcomes[J]. JAMA Surg, 2018, 153( 11): 1057- 1059. DOI: 10.1001/jamasurg.2018.2614. [22] Working Party of the Australasian Pancreatic Club, Smith RC, Smith SF, et al.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Australasian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ncreatic exocrine insufficiency[J]. Pancreatology, 2016, 16( 2): 164- 180. DOI: 10.1016/j.pan.2015.12.006. [23] HOLLEMANS RA, HALLENSLEBEN NDL, MAGER DJ, et al. Pancreatic exocrine insufficiency following acute pancreatitis: Systematic review and study level meta-analysis[J]. Pancreatology, 2018, 18( 3): 253- 262. DOI: 10.1016/j.pan.2018.02.009. [24] DAS SLM, SINGH PP, PHILLIPS ARJ, et al. Newly diagnosed diabetes mellitus after acute pancreatit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Gut, 2014, 63( 5): 818- 831. DOI: 10.1136/gutjnl-2013-305062. [25] IQBAL U, ANWAR H, SCRIBANI M. Ringer’s lactate versus normal saline in acute pancreatit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Dig Dis, 2018, 19( 6): 335- 341. DOI: 10.1111/1751-2980.12606. [26] CROCKETT SD, WANI S, GARDNER TB, et al. American gastroenterological association institute guideline on initial management of acute pancreatitis[J]. Gastroenterology, 2018, 154( 4): 1096- 1101. DOI: 10.1053/j.gastro.2018.01.032. [27] LIPINSKI M, RYDZEWSKA-ROSOLOWSKA A, RYDZEWSKI A, et al. Fluid resuscitation in acute pancreatitis: Normal saline or lactated Ringer’s solution?[J].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5, 21( 31): 9367- 9372. DOI: 10.3748/wjg.v21.i31.9367. [28] YI FM, GE LQ, ZHAO J, et al. Meta-analysis: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 versus total enteral nutrition in predicted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J]. Intern Med, 2012, 51( 6): 523- 530. DOI: 10.2169/internalmedicine.51.6685. [29] STIGLIANO S, STERNBY H, DE MADARIA E, et al. Early management of acute pancreatitis: A review of the best evidence[J]. Dig Liver Dis, 2017, 49( 6): 585- 594. DOI: 10.1016/j.dld.2017.01.168. [30] ADIAMAH A, PSALTIS E, CROOK M,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pidemiology, pathophysiology and current management of hyperlipidaemic pancreatitis[J]. Clin Nutr, 2018, 37( 6 Pt A): 1810- 1822. DOI: 10.1016/j.clnu.2017.09.028. [31] CHRISTIAN JB, ARONDEKAR B, BUYSMAN EK, et al. Clinic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bserved when follow-up triglyceride levels are less than 500 mg/dL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hypertriglyceridemia[J]. J Clin Lipidol, 2012, 6( 5): 450- 461. DOI: 10.1016/j.jacl.2012.08.007. [32] WU XZ. Academician wu Xianzhong’s collection[M]. Beijing: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2014.吴咸中. 吴咸中院士集[M].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4. -

 本文二维码
本文二维码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2590
- HTML全文浏览量: 545
- PDF下载量: 463
- 被引次数: 0


 PDF下载 ( 949 KB)
PDF下载 ( 949 K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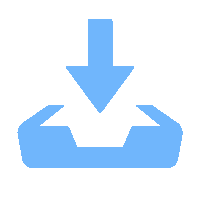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