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Bilir BM, Guinette D, Karrer F, et al.Hepatocyte transplantation inacute liver failure[J].Liver Transpl, 2000, 6∶32-40.
|
|
[2]Strom SC, Chowdhury JR, Fox IJ.Hepatocyte transplantation for thetreatment of human disease[J].Semin Liver Dis, 1999, 19∶39-48.
|
|
[3]Kobayashi N, Ito M, Nakamura J, et al.Hepatocyte transplantationimproves liver function and prolongs survival in rats with decompen-sated liver cirrhosis[J].Transplant Proc, 1999, 31∶428-429.
|
|
[4]Kobayashi N, Fujiwara T, Westerman KA, et al.Prevention of acuteliver failure in rats with reversibly immortalized human hepatocytes[J].Science, 2000, 287∶1258-1262.
|
|
[5]Weglarz TC, Degen JL, Sandgren EP.Hepatocyte transplantation in-to diseased mouse liver.Kinetics of parenchymal repopu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proliferation capacity of tetraploid and octaploidhepatocytes[J].Am J Pathol, 2000, 157∶1963-1974.
|
|
[6]Selglen PO.Preparation of isolated rat liver cells[J].Methods CellBiol, 1976, 13∶29-83.
|
|
[7]Suzudi A, Zheng Y, Kondo R, et al.Flow-cytometric separationand enrichment of hepatic progenitor cells in developing mouse liver[J].HEPATOLOGY, 2000, 32∶1230-1239.
|
|
[8]Kubota H, Reid LM.Clonogenic hepatoblasts, common precursorsfor hepatocytic and biliary lineages, are lacking classical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classⅠantigen[J].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0, 97∶12132-12137.
|
|
[9]Hirose T, Yasuchika K, Fujikawa T, et al.“Blastophere”:a newculture method for human fetal hepatic progenitor cells[J].Gastroen-terology, 2002, 120 (Suppl1) ∶A-542.
|
|
[10]Kamiya A, Kojima N, Kinoshita T, et al.Miyajima maturation offetal hepatocytes in vitro by extracellular matrices and oncostatin M:induction of tryptophan oxygenase[J].HEPATOLOLY, 2002, 35∶1351-1359.
|
|
[11]张淑莲, 曾平鲁, 肖荣, 等.肝干细胞分离培养条件的筛选[J].肝脏, 2003, 8 (1) ∶31-32.
|

 本文二维码
本文二维码


 PDF下载 ( 293 KB)
PDF下载 ( 293 K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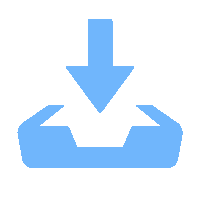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